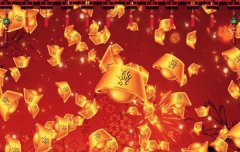不要喊新冠患者“羊”疾病歧视会让我们变成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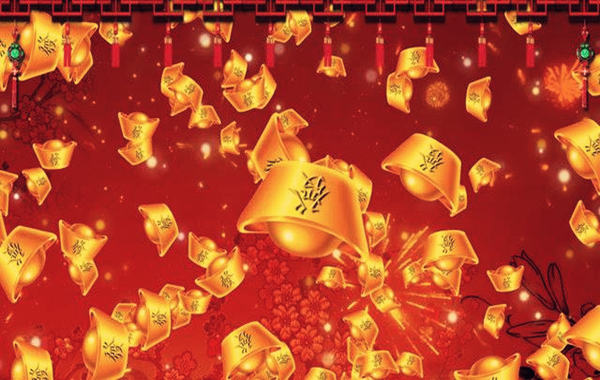
日前,媒体报道了上海部分新冠肺炎康复者的困境,他们康复后离开方舱,却在小区门口被拒绝入内;他们被称呼为「羊」「小阳人」;一些人即使成功返家,也会遭遇邻里冷眼。
报道提及,一位 66 岁的老人离开方舱后,被小区拒之门外,她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中,已经住了 22 天。
有关新冠肺炎的病耻和歧视,是人类对传染病歧视的缩影。从麻风、天花、肺结核、肝炎到 COVID-19,这些不同时代流行病的爆发伴随着强烈的病耻和污名。
污名可能来自对病毒、传染源的科学认识或者其他无法忍受的不利情况。人们认为,只要远离威胁(感染者),就会获得安全。
人们也因此被分为「我们」和「他们」。这种逻辑可能还有另一层 ——「我们不是他们(感染者),我们没有相同的风险因素,所以我们没有危险」。
污名最常见的一个行为是,寻找归因 —— 即使这种原因可能并不真实存在或并不相关。找到罪魁祸首,将一种神秘可怕的疾病变成有形和可控,可能会暂时减少焦虑。
于是,传染病爆发之下,人们下意识寻找替罪羊,将疾病归咎于对方的不负责任或不良道德。
在疾病污名的偏见和歧视下,被波及的不只是患者,还有他们的照护者、家人甚至医护人员。遭受污名的不只是个人,在过往的流行病中,社群、种族、性别、居住地、文化可能都被放置于污名化的风险中,招致羞辱。
麻风,这种现存最古老的瘟疫,与人类相处可能超过 3000 年。千年以来,麻风的病耻在全世界通行,患麻风病则被认为是「不洁净」和「恶行」。
时至今日,我们和麻风病的斗争已经取得胜利,但和疾病污名化的抗争仍在持续。
因为肢端神经受损,麻风病人对于肢端的疼痛并不敏感。缺少了这种警示性的疼痛感觉,即便意识清楚,患者因为知觉缺失也很难觉得这是自己的躯体,因此过度使用肢体,最终导致截肢之类的残疾。
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磺胺类药物和氨苯砜的应用使治愈麻风病成为可能。如今麻风病已经可被联合用药疗法( MDT )完全治愈。
事实上,麻风病的传染性并不强,在我国的传染病分类中被划为丙类,与流行性感冒同级。
讽刺的是,麻风病被视作宗教罪恶的同时,在 19 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中,比其传染性和致死率更高的肺结核,却作为「文雅、精致、敏感」的象征,变成了一种时髦。
由此可见,在当时,麻风歧视的起源并不在于其传染性,而在于它对患者外表的毁损。病人身份和不同肤色的面孔一样,直接可以看见其与「社群中的多数」有所不同。
在 1873 年之前,麻风的罪魁祸首 —— 一种革兰氏阳性菌麻风杆菌还没被发现的漫长时间中,麻风被认为是「不洁净」和「恶行」的象征。
20 世纪以前,麻风病人一旦得病则需穿上黑袍,挂上铃铛,过上清教徒的生活,用苦修来「治愈」疾病。
至今,我们仍然能从西方流行文化里的巫婆角色中找到猎巫时代麻风的影子;麻风病人 Leper 这个单词,仍可用以指代「被憎恶和遗弃的人」。
公元 12 世纪,英国国王亨利一世颁布的针对麻风病人的法令中,规定麻风病人「金融财产被冻结,不能享有财产继承权, 甚至不能提出诉讼。」这与其他基督教国家大同小异。
1996 年日本才废除《癞病预防法》这一歧视性法案,这部法律曾把限制、关押流浪的麻风病人合法化,并且强制病人堕胎,胎儿放到实验室做标本。
关于麻风村、麻风院和麻风岛的记载,不可计数,至今仍是人类学中的重要话题。诸如麻风岛,麻风村等社群的存在,一向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所钟情的研究对象。
用以专门管理传染病的防治中心是大众普遍避之不及的。感染科在医生的职业选择中也往往不那么受欢迎,因为「待遇偏低」,也有人觉得「危险」。
1882 年 3 月,来自中国福建的劳工 Wang an Chin 登上美洲这个世界岛屿的时候,并没有罹患麻风。
他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强制预防接种计划,又正值盛年,Wang an Chin 大体是一个健康的人。然而他很快就明白,在旧金山,有没有患病这无关紧要。
尽管英国人给中国人带来了鸦片,西班牙人为美洲带去小儿麻疹、斑疹和伤寒,毗邻的墨西哥的麻风病例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在旧金山,这些疾病都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过错。
在 19 世纪初,美洲的华人劳工被视为廉价而受欢迎的替代劳力。然而,1870 年之后接连发生的经济萧条和主城区天花疫情,使当局迫切地需要推卸执政不力的责任。
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上的溃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海外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尽丧。集合了外来者、异教徒和弱国穷人身份的华人就如中世纪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一般被选中为替罪羊。
当局把经济萧条导致的失业归咎于中国人用低价抢走了职位,靠欺诈夺取了财富;又称重燃的疫情是因为「奸诈而爱说谎的外来者不遵守清洁规则,罔顾美国人民的健康福祉」。
在病菌致病的理论尚未被广泛接受的 19 世纪,遗传论和进化论主宰民众对疾病的认知。
在当时,麻风病在宗教意味之外,被另外赋予了文化和文明上的意味。它首先被认为是穷苦人的病,下等人的病。两者融合,成了反映「外来者试图和高加索人种过上同一种生活」的僭越罪行的病。
中世纪的麻风病被作为道德的准绳,而在新世界,它则变成了划分落后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界限。
彼时在中国,麻风歧视虽然没有强烈的宗教象征,但是却和德行,以及不守妇道妇女的性接触相关联,由此而具有强烈的社会象征,并被认为可以遗传。
在近现代中国,麻风被视作南方的「风土病」,是因为南方虫疬病瘴,被视作是远离中原正统化外之地,穷乡恶土的疾病。而在西方人眼中,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南方人」。
中外对于麻风认识微妙的相合之处,使西方以其为出发点的文化欺凌甚至在中国也被民众半信半疑地接受。
惨痛的半殖民地历史和孱弱的国力,使中国的麻风污名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殖民记忆。事实上,这也是同时期其他殖民地的共同经历。
而正是基于此,无论是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还是之后建立的新中国,都将麻风的防控视为一件事关国体的大事。
香港学者梁其姿在其著作《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中讨论了麻风在现代化国家治理建构中的意义:消灭麻风不单单使得重构权力体系的新中国重新走入西方藉由落后和现代二分法构建的形象体系里的国际社会体系,也助推了中国基础卫生系统的发展。
经过数十年持续的努力,麻风已渐渐在中国消失。但将传染病政治化并将其作为政体合理、合法性的依据的讨论,时至今日,依然令我们心有惕息。
2012 年 6 月 18 日,美国众议院作出决议,以立法形式为 130 年前颁布的《排华法案》进行道歉。
然而至今,针对麻风和其他传染病的偏见,以及针对华人的污名,依然是隐约漂浮在美洲大陆上的阴霾。
2020 年 2 月,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时,《华尔街日报》发文「现在中国人是真正的东亚病夫了」。文中将新冠疫情归罪于「带有跳蚤的蝙蝠病毒」,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制度,并称该疾病的流行「将引发产业上的去中国化」。
正如百年前来到美洲大陆的华人劳工所面对的麻风污名一般,新冠疫情的爆发和病毒传播者的污名,海外华人甚至整个亚裔群体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频繁地使用「中国病毒」( Chinese Virus ),激起了华裔群体的抗议。在罗马,一些商店贴出告示,「不接待中国顾客」。一位日本音乐家在纽约因为「长得像中国人」被打成重伤。
据纽约市警方,自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共有 1200 桩针对亚裔的种族仇恨案件发生,而目前正在调查的 15 宗仇恨案件全部指向亚裔。
新冠肺炎爆发初期,「湖北」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在封城之后,网传在封城前夕逃离的武汉人使「鄂 A 」及湖北籍车辆成为排查重点。
在疾病防控手段之外,还有被房东驱离的湖北打工人,有「酒店不让住了」的湖北家庭,也有想要进城处处碰壁,在高速上流浪一月余的湖北籍货车司机。
这样的偏见和歧视,一直持续到复工复产,即使在湖北地方疫情业已平息,多日新增为 0 的情况下,湖北籍人士依然被大量地劝返和拒绝。
在新冠疫情早期,「湖北出身」和「鄂 A 车牌」,犹如麻风病人身上的铃铛,带来了具有污名色彩的身份辨认。
在疫情早期的社交媒体,不乏要求湖北人致歉的言论。即使感染溯源仍没有确切的结果,湖北人却几乎默认了「湖北人都是病毒传播者」的污名,甚至有当地居民主动要求更加严格的隔离措施,来「降低危害」。
两年之后,类似的情况一再出现。有人称阳性感染者为「羊」,感染者被带离小区被称为「赶羊」。
根据《冰点周刊》 2022 年 5 月 6 日报道,一位租住在上海小区的老人在离开方舱后,被转运回小区,进不去了,「小区说再发现阳性又要 14 天」。
她讨要说法,得到的答复是,她租住的房间属于「违章建筑」,要清退,她不属于小区居民。
66岁的老人如今寄身在一处拆迁区巷子里的帐篷中,门帘是青色的编织袋,床垫是一层一层纸箱壳。
在疾病污名的偏见和歧视下,被波及的不只是患者,还有他们的照护者、家人甚至医护人员。
根据世界各地的报道,因可能面临的污染风险,医生和公共卫生从业者与亲人隔离,但仍因恐惧和污名,遭遇身体或情感上的攻击,这使得本已严峻的形式更具挑战 ——长期的社会误解可能导致公共卫生资源比例分配不均。
被污名的人群可能因为缺乏准确的信息,他们预判自己可能遭遇歧视,从而抗拒诊断检查,降低了治疗的依从率。也可能不信任公共卫生建议,在发生社会卫生紧急情况时拒绝合作。
「我们」以为不会成为「他们」,但疾病歧视和恐慌之下,谁能说,自己永远不会被波及呢?
在每一次流行病中,都不断出现这种情况: 将疾病和种种社会问题的不幸归罪于某一群体。
正如中国人在麻风传播问题上所蒙受的不白之冤,类似的还有,吉普赛人长期被与「黑死病」联系到一起,与华人劳工同时期的意大利移民也被视为小儿麻痹症的「病因」,犹太人被视作是结核和黑死病的「特定宿主」。
与传染病相关联的歧视在种种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已然变成一个庞然大物。有关麻风的病耻和歧视,其实只是广泛存在的对传染病的歧视的缩影。
值得欣慰的是,在医学的发展下,麻风病等在旧时代强烈威胁人类文明的传染病正在加速消亡。如今,麻风病在全球的发病率为每万人 0.29 例,而这个比例还在进一步地下降。
麻风病药物治疗方式的出现,对于改变麻风病人的处境和消除污名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它不仅仅减少了病例,「人类能够解决,掌控这种疾病」的认识,也使公众认知中的麻风病人的「危害性」,大大降低,以健康利益冲突为基础的污名的动机因此减少。
如今,病例的鲜见使得「麻风」这个词汇在千禧一代中近乎消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对麻风病彻底遗忘。迄今为止,仍有 20 多个国家存在麻风歧视性法案。
忘记传染病病人的身份标识,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中,去寻求平衡,只表达爱而略去仇恨,似乎是一件难事。
在信息化的时代,观点的对峙更加激烈。这也导致对传染病患者的污名可能披着「公共利益」的外衣,变得更为尖锐。
对于麻风病,世卫组织一直鼓励使用其科学称谓「汉森氏病」 ( Hansen’s disease ) 而非「麻风病」( Leprosy ) ,意在淡化隐喻,消除污名。
古老而衰微的疾病麻风,是传染病污名化的先辈和集大成者。麻风的历史,就是复杂而残酷的人类社会变迁史。
[3] 《2016-2020年全球麻风病战略:加速实现无麻风世界》世界卫生组织